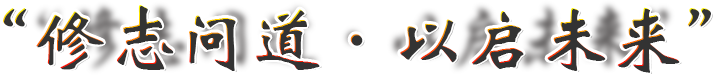飞白书传人——吴少白
长春隐逸着一位飞白书名家,并集绘画、收藏于一身的大师。于是,强烈的感佩心理驱使我亲临他的兰雪堂拜访,他就是飞白书传人——吴少白。
飞白传人
吴少白,字兰雪,号白榆。生于1937年,祖籍京东乐亭。有家学渊源。父亲是“飞白书”爱好者,对他有很深的艺术影响。儿时的吴少白对飞白书即有浓厚的兴趣,且思学若渴,每逢父亲伏案习字时,他便侍立案头,默默凝视父亲如何运笔。久之,逐渐悟出飞白书之要,即在“转、折、顿、挫”四则。每看父亲练笔之后,他几乎都悄悄找些用过的纸在背面实践。米靠碾,面靠磨,遇到问题靠琢磨,边练边琢磨。然而,此时他对飞白书了解不深,不过处于盲人瞎马而已。可是父亲看到儿子如是潜心研习,书法日有所进,自然打心眼儿里高兴,并预感到这孩子将来或许对飞白书有所成就,便抽空儿将张燕昌的飞白书四要“转、折、顿、挫”向少白传授。
转:围法也,有圆转回旋之意;
折:笔锋欲左先右,往右回左也(飞白书往右宜作燕尾状,不回左),直画上下亦然;
顿:力注毫端,透入纸背,笔重按下;
挫:顿后以笔略提,使笔锋转动,离于顿处。
唯此四法则……是书既用渴笔,其墨甚轻,转折顿挫,显而易见。不特所谓“飞中白,白中飞”者显之于此,即所谓“轮囷萧索”“轻若丝发,重如云山”……凡莫不以转折顿挫四法书之。其关运笔之重要,概可想见。
在父亲弥留之际,童年的少白侍立于病榻前。老眼昏花的父亲眸子呆滞地看着儿子,强忍病痛,语重心长地嘱咐:“飞白书乃我中华的瑰宝。自东汉以来,炎黄子孙世代相传,从未间断,传至如今,不晓得有无承袭者。无论如何,倘若你能当此重任,使飞白书延续下去,我将来在九泉之下,也无所挂记了!”……
遵照父亲临终时的遗愿,十二三岁的少白临摹王羲之的书法,同时开始自务绘画。他从小就肯于吃苦,朝夕执着投入,虽然付出太多的憨劲,但因为没有名师指点,走了好多弯路……二十左右岁的时候,少白以继承父亲的遗志为己任,经过近十年之涉猎研习,广搜博采,吸纳精华,积累所学,功夫不负有心人,书画终于崭露头角,飞白书尤为人瞩目,并很快闻名遐迩。
飞白书创始于东汉左中郎蔡邕,字伯喈,文学家,书法家。书家小传:“灵帝熹平四年,诏邕以李斯、曹喜及古今各体书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白土,泛指可用来涂饰的土。)帚成字,心悦之,因归而作飞白之书。”自此,汉、隋、唐、宋、金、明、清,历代名家层出不穷,兹将代表者荐引一二共享。
王献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论书表》:“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帚,沾泥汁,出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之,叹美,问谁所作,答云七郎。于是羲之作书与亲故云:‘七郎飞白大有意。’”张怀瓘古贤能书录:“神品飞白三人:蔡邕、王羲之、王献之。”
武则天,名曌,高宗后。《不墨镌华》:“升仙太子碑首‘升仙太子之碑’六大字,飞白书作鸟形,亦佳。飞白书久不传于世,此其仅存者耳。”
苏轼:文与可飞白赞
呜呼哀哉,与可!岂其多好为奇也欤?抑其不试改故艺也?始于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隶、篆也,以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异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乎其远而想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至今乃得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心;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呜呼,哀哉!
清人陆绍曾等辑《飞白录》,收入从汉到清历代书“飞白”者凡102人。现如今,大师吴少白当为飞白书第103位传人。
刚直不阿
后来,吴少白走出家乡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谋份工作,由于他能写一手好字,既会写文章又善绘画,很快任秘书并兼工会宣传工作。年轻肯干,工作挺出色。不久,被组织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在他的人生旅途中,这个阶段可谓是一路顺风。
但,他突然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便请假回故里奔丧。办完丧事,假期已超,返回单位时,领导认为他因家事影响工作,身为预备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便批评了他。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因为他当时正值服丧之际,原本情绪不好,再一挨批评,不啻火上浇油。如鲠塞喉,一时气愤,什么党籍、公职全部不要了,拂袖而去,跑到乡下务农去了。
领导就是领导,说归说,做归做,有几个领导真正能从心底里为属下的政治生命、生计负责,心平气和,耐心细致地做做工作,使其心服口服正视自己的问题,从而归队继续工作。诚如凤毛麟角啊!
而吴少白当时倘若跟领导顺情说说软话或者“上点儿”。不仅不会丢了工作,依他的才能与干劲儿,或许会腾达起来。可他的脾性是宁折不弯的,致使他的一生再也没有公职,一生没有固定收入,一生没有生活保障,但他从没因此而懊悔。
而立之年以后的少白,书画的功底既厚且实,尤为圈子里的名家所瞩目。有人建议他入书法家协会,这也是他的夙愿。当他向有关部门咨询需要哪些手续时,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回答既干脆又随意:“你真够刻板的,什么手续不手续的。摆一桌,请相关的喝个痛快就得了!”这或许是笑谈,可他听了一愣,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在他的心目中,协会是清水衙门,是挺庄重、挺受人尊重的地方,门槛儿很高,听这位一说,所谓的协会原来如此的荒唐,如此庸俗,让他很失望,他以为,应该凭作品的水平,凭成果多少,经过专家评审,决定可否吸收入会。如果凭请客,岂不是以贿赂交易的会员资格吗!这样的话,那“会员”的称呼就一文不值了。不要说别人,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他很固执,从此远离什么协会、学会之类的组织。
素有“狗跟屁走,人跟势走”之说,他一向看不起那种阿谀奉承的马屁精。从此,他不为权势而折腰,凭几只笔活命,活得仗义,活得坦然,活得自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浪迹天涯。
唐山地震
1976年夏,吴少白原本就不是务农的料儿,握着锄头、镐把,总不如握笔杆儿自如、惬意。于是,他离开乡村到唐山一家陶瓷厂,以其一技之长画瓷。总算复归了他热爱的书画专业。当时,正逢全国大搞“红化”活动,唐山大街小巷两侧的画廊、墙壁也当然就出现“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万岁”“斗私批修”等标语和社会主义新气象之类的宣传画。吴少白能写善画,必然被派上用场,大显身手。因为他分担的工作量太多,难以如期完成任务,便请当地京剧团制作布景的一位朋友帮忙。每天傍晚收工后,吴少白都自掏腰包买些酒、五香花生米、熏豆腐干儿之类下酒的菜犒劳人家。他向来酷嗜饮酒,并形成个人独特的交友观:“不饮酒者,心肠不热,不值得一交。”大概是这个意思。
一天晚上,吴少白照例买些酒菜在自己的寓所里与朋友共饮。二人边饮边聊,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人逢知己千杯少”,一直喝到翌日凌晨一点钟才作罢。那位酒友走后,他的酒劲儿愈发上涌,浑身散发出浓浓的酒气,云山雾罩,晕头转向地一头便扎到床上。顷刻间,哧儿呼地进入梦境,继而,沉雷般的鼾声大作……
唐山阖城居民正沉睡在梦乡,哪知道,死神的魔爪已悄悄地伸向他们。凌晨三时许,突然大地颤抖起来,颠动得像粮米在簸箕里簸起来一样,房屋、大楼、烟囱,所有的建筑物都在摇动,仅仅几秒钟的工夫,一场罕见的破坏极强的大地震发生了!顷刻间,整座唐山市变成一片废墟。满目瓦砾,满目疮痍,死一般沉寂,一派凄凉、灾祸景象。据悉,伤亡近30万人,财产损失非常惨重。
不知是大地的颤动,还是地震的巨响惊醒了吴少白,微睁惺忪的睡眼一看,房盖塌了下来,梁柁一头仍然搭在墙上,一端戳到地上。他的醉酒、睡意倏地全给吓醒了。他立马睁大了眼睛,寻找逃生的出口。他小心翼翼地下床爬向房门,但房门被倒塌的墙堵得严严实实;再爬到窗前,依稀还有点儿缝隙,他便奋力扒开砖头瓦块,又启开窗子,总算寻到一条逃生之路。
他逃出倒塌的房子,环视一遭才知道发生地震了,不由得涌起一股失落、背运感。不禁仰天长叹:“咋这么点儿低,走哪,哪出事。我吴少白该不会像姜子牙吧,一辈子不走运!”转而又一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学然后知不足。吴少白的书画虽然经多年努力已具厚实的功底,可是他还觉得远远不够。他想,长春这个地儿,原来是伪满的京都,藏龙卧虎,很可能有书画界的名人。为使自己的书画技艺精益求精,他便决定到长春寻师访友,兼出手个人的作品。一下火车便在站前打听,长春哪个地方富裕。可能问得不委婉,欠客气;也许遇上了玍古的街头小混混儿,跟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答曰“八里堡”。殊不知,此地如本城的二道河子、宋家洼子,都属于“贫民窟”“杂八地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聚集之地。哪里会有书画的高人;谁能有闲钱买书买画?让吴少白大失所望,短暂地落下脚儿便离开了这个鬼地方。后来,他又听说城东有个净月潭,搞艺术的人都想去那里找点儿浪漫色彩,于是慕名前往,才知道,此处依然不是他向往的地方。当时,他一筹莫展,颇有琴剑飘零之感。
名家题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书画是吴少白一生的追求。宁可不吃饭,也不放弃书画。无奈中,他萌生了去上海闯荡闯荡的念头。目的还是一访书画界高人,二展示个人的作品。多年来,他一向是“以书画养生,以生而求艺”。他想,大城市名家多,作品或许好出手。他是个性急、务实的人,奔上海的心愈切,于是匆忙启程。
1993年,吴少白客居上海时,正逢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即将召开。他不失时机地与会当场挥毫,为东亚运动会捐赠作飞白书与国画,博得众多围观者频频竖大拇指,啧啧赞叹。仅几幅书画即拍卖人民币数万元。继而,东亚运动会组委会向少白颁发了荣誉证书,并幸得上海书法报刊关注,先后以题为《即书即画飞白绝艺》《传统飞白书后继有人》两篇文章发表。
吴少白初次到上海不虚此行,让他感到庆幸的是,客居此城不久,就拜上海国家级著名书法家、103岁的老人苏局仙为业师。
紧接着,吴少白因势利导,于大上海在业师苏局仙与友人鼎力相助下操办个人书画展。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有的争选其旧作,有的愿当场欣赏其泼墨作书绘画,大饱眼福的同时选购作品。出乎预料,书画展办得超出想象的成功,既有力地宣传了自己又获得了经济效益。
两次活动,吴少白及其作品在上海名声大噪。从而,上海人知道京东乐亭有位多才多艺的飞白传人,并荣膺上海十几位书画界名人的高度赏识与评价:
著名书画家胡成荣先生题鉴“妙笔生辉”
著名书画家许仕骐先生题鉴“笔歌墨颂东风”;
著名书画家张大千弟子黄达聪先生题鉴“富艳精工”;
苏局仙老人题鉴“吴氏飞白”,并赋诗赞赏:“即书即画悟禅机,艺苑当今却是稀。拒扼十年深有得,一朝展出誉腾飞。”——题“吴少白书画展”,南汇百三岁老人苏局仙。
上海著名诗人、书画家82岁老人施南池和苏老韵题赞《吴少白出示大作,即和苏局仙老原韵奉题》:“挥毫书画出天机,神妙新奇海上稀。翰墨姻缘真可喜,凭窗拜读兴腾飞。”
另,吴少白以飞白书录南北朝鲍照“飞白书势铭”文章。施南池老人为之题赞:“少白飞白妙绝伦。”儿此种种,不一而足。
故地重游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老师天南地北,四海为家。历尽艰辛,对艺术孜孜索求,终有所成。他的书法,楷、行、草、隶、篆皆高人一筹,尤以飞白书、竹叶字见长。他的绘画,花卉、人物皆不凡,更以肖像、竹殊佳。飞白与竹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1996年,吴老师应长春某高校之邀,加之此城有多位至交,便又欣然来到春城。大概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此来,有一桩命中早已注定的美好姻缘默默、神秘地等着他。这是后话。照例,他依然客居朋友家。说到朋友,要赘述几句。吴老师的书画,20世纪80年代在长春就备受关注,尤其是爱好书画的市民,多喜欢与之交往,其中有几位居然成为他的莫逆之交,张连春就是之一。吴老师在他家一住就是几个月,不分彼此,相处如一家人。
同年数月后,吴老师果然在长春成了家。婚后,他并非陶醉于安怡的小家庭,照样笔耕不辍,作书作画。近古稀之年的吴老师边整理一些旧作,边撰写《我和飞白书》《飞白书七体千字文》。为飞白书与竹叶字——中华文化瑰宝得以世代相传,老人家甘愿将毕生所学传授后人。信息一经传出,前来报名的学童络绎不绝,多达40余人。老人家无可瘟耍映闪募页っ侨惹榈卦郑αο嘀河械奈怕藿淌遥挥械奈阶酪巍页っ恰巴吨蕴摇保饫鲜Α氨ㄖ岳睢薄K贩芽嘈模闫渌芙淌冢惺保踔劣谑职咽值匾槐室槐实亟獭9Ψ虿桓河行娜耍行┑茏泳改甑呐Γ蕴爻ど既爰忠帐跹г海绻⑿隆⑽夂婆舻取E砘持揪谷蝗倩袢嗌倌晔榉ù笕谝幻岬昧私鸾薄�BR>
从此,老人家在春城名垂竹帛,多家媒体频频采访、报道,应接不暇。
1991年,四川江油太白碑林征稿,吴氏飞白书入选两幅,镌刻入碑;
1997年,长春电视台专题采访吴少白的飞白书,并录以存;
1998年,《长春晚报》《城市晚报》《吉林日报》《东亚新闻》《新文化报》等相继采访、报道;
2005年,中央三台《音画时尚》建台五周年,选登飞白书与行书展示,有吴少白两幅作品;
2006年春,湖南卫视专程来长采访吴少白。与此前后,吉林电视台的《吉林新闻》《都市频道》《吉林名人》等也相继采访吴少白;
台湾《海峡颂》节目主持人、编辑邀请吴少白以飞白体书写“文清”“高洁”等名字馈赠。他的飞白书还走出了国门,日、英、美、澳大利亚等国皆有老人家的手迹,或书其名,或录诗词,约有数百幅。
淡泊名利
吴老师不仅书画卓越,还酷爱古玩。他未经专门学习,也没谁指点,单凭自务,久而久之,功到自然成,对古玩与收藏很专业,可谓专家。无论哪朝哪代的古玩,他搭眼一瞧或伸手一摸,即可辨真假。多年来,或以飞白书、竹叶字,或以竹、肖像等作品易得相应价值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古玩达数百件,略估价值人民币近亿元。
一进吴府的门,便令人眼前一亮,除了书画就是古玩。吴老师的工作间兰雪堂里,置一偌大的古董柜,摆放数十件价值连城的珍品。大厅、居室、餐厅、厨房、甚至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古玩。百余平方米的房间,五光十色,古色古香,蓬荜生辉。迄今,老人家珍藏的几百件古玩,件件都视为自己的心肝宝贝。即使有时手头再拮据,也不割舍外流,一件也不出售。
一辈子追求,敬业于书画的大师哪有古董商那种狡诈的心计与手段。淳朴、敦厚的吴老师虽两次被骗,他的珍贵的经名家题鉴的作品,被浙江余姚某古董店的老板骗去。另一起,经名家题鉴的书法作品五幅,画百幅,竟被吉林某业内人士谎称为之拍照带走了,至今人物不见。对此,老人家不屑一顾,并戏言:“稀罕就说一声,拿去算了,何必动脑筋绕那么大的弯子,不累吗!”
漠视名利,吴老师对名家为其书画作题赞;对于多家媒体登门来访,从不以为然,并认为是身外之物,无所谓的事情;对于书画展,即使在大上海的展出,且博得观众、名家的美誉,绝不沾沾自喜。有的倒是,自我吹毛求疵,找问题。他一向认为,人一旦被名利索绊住,就会变得浑浑噩噩,一事无成。远不如低调地过那种清静、平淡的日子。
定居春城
吴老师来长春定居已近花甲之年,再走南闯北地奔波,纵有旺盛的精力也未必身能由己。一年老似一年,身边也该有个人照顾了。其实,他虽先后娶过两房妻子,发妻还生了一男一女,二房有两个女儿。皆因其穷,相继离异。落得他至今只身一人东跑西颠地闯荡。
于是,长春的朋友们为他张罗遴选伴侣。女方大红媒介绍王莉的情况:中学毕业,时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了一条当时青年们下乡插队的必经之路,返城当了车灯厂的工人。婚后有一男一女。不幸,中道琴断朱弦。命运不济的王莉以每月二千元工资带着两个孩子,并相继送他们上学读书。孩子虽有叔、伯、姑,但都是低薪,爱莫能助。这种日子如何熬过来的,其艰难可想而知。一次,因意外急需,王莉到至亲家欲借30元钱。为了讨好人家,去前还特意紧紧手买了一盒点心,却讨了个没趣儿。钱没借到,却看人的冷脸色,说三道四,让她深切感到世态的炎凉。
有人来提亲,孀居孤寂多年,时值45岁的王莉一时动了心思。男方介绍人挺干脆也很实在,说吴老师58岁,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没有固定收入,以书画为生计。但却有一手能书善画的绝技,可谓“法宝”。就看王莉有没有胆量嫁给这样的人了。
王莉当时的心情如千丝万缕绞在一起,乱作一团。她不能不严肃、谨慎、认真地将这团乱丝理顺。已经走过来的路告诉她,人生依赖谁都是不可能的,靠谁也不如靠自己。含辛茹苦把一双儿女将养大,现在都已成家立业,不仅对得起子女,也对得起他们九泉之下的父亲。然而,这些年有谁能设身处地地理解自己的苦衷:即当父亲又当母亲养育儿女和经济入不敷出的困苦。孤独、凄凉度日如年;渐渐步入老年,身边朝夕有个人相伴未尝不可。可是,伊人的年龄未免大了点儿;没有劳保,还得养活他……思来想去,心地善良的王莉,最终还是同情心占了上风。转而,她倒非常体念吴老师的处境,尤其他晚年的生活与归宿。她终于横下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也许是缘分吧,1996年8月的一个良辰吉日,两个人在众亲朋好友的热烈祝贺下,结为秦晋之好。从此,吴老师不再颠沛流离,不再客居友人之家。从此,他有了固定的栖身之所——自己的家。从此,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为他烧饭洗衣……
长期过日子哪有舌头碰不到牙的,天长日久,夫妻间也会闹矛盾。况且,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大、性格各异、阅历之殊、素质不同……诚可谓天冠地履。更何况,一位是声名籍甚的书画大师,一位是普普通通天生质朴的“知青”工人。一个是所想所为多为高雅精神境界、理想主义带点儿浪漫。据说,凡才华横溢者,每每性情怪僻。一个是很现实、要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对于伊人的潜质,非凡才艺的价值熟视无睹。对于伊人珍藏的古玩,在王莉的心目中,房间原本有限,古人留下的盆盆罐罐,奇形怪状的石头……七百年的谷子八百的糠弄到家里来有什么用?神经病!这中间,偏偏有人来添乱,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吴老师得意的作品,轻蔑地脱口而出:“这玩意儿有啥用?能值几个钱,顶吃顶喝吗?”吴老师在一旁听了火冒三丈,如鲠卡喉。依他的刚直倔强的性格几欲反唇相讥,但又一想,不知者不为怪,此人知识贫乏得可怜,暗想“井蛙不可以语海”,也就心平气顺了。因之,在他们的生活中难免出现小摩擦。往往彼此怄气拌嘴有之,一时失了和谐有之。但好在性格直爽的王夫人、禀性豁达的吴老师,茏猿帧⒆跃蹋夷芑ハ喟荩嗷ヌ辶拢淘莸男∧Σ凉ブ螅惶斓奈谠平陨⒘恕7蚱拗湓谟谀ズ希灰舜颂钩舷啻Γ突崮ズ铣龀志玫陌椤�BR>
1997年5月,吴老师为事业又赴上海。几天后,想到往家寄封信,通篇是感人肺腑之言,洋溢着诚挚、热忱的气氛:
“这么多年我没有家,我像只海鸥,也像流沙……在旅店,感到孤寂,想起你,我没有负起丈夫的责任,深感愧对了你……每天要坚持晨练;吃好饭;灰指甲,每天上两次药……”
信的内容不多,话也挺朴实,但句句掏心窝子。犹如老父对儿女的呵护,又像大哥对小妹体贴入微的关怀。去上海,他只带了500元的旅费,一路上省吃俭用,节约的钱为王莉及其儿女买了内衣、鞋子。行,往往胜于言!
赤诚、磨合、感化,虽为半路伉俪,也不啻青梅竹马的结发夫妻。
渐渐的,王莉终于意识到丈夫的书画和古玩的意义和价值,并自觉自愿地参与丈夫的事业。作品多通过她的手装裱。有时,吴老师买古玩,赶上缺个零头,她便主动付出,作个小投资。
赶上王莉过生日,吴老师在生日宴会上即兴画竹、画兰,并吟诗一首:“十月阳春胜似春,栽下竹枝像知音。今日相对无虚言,高山流水夜夜新。”
王莉听了非常高兴和感激,乐得嘴都合不拢,不知说啥好了,脱口称丈夫“像个老顽童”!
彼此常相思,常相忆,老来有个伴儿,相依为命,知疼知热。这份夕阳情诚宝贵!这份晚情值得珍视。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若投机万言不为多。我与少白老师应酬间,宾主同气相求,彼此倾心吐嘱,纤毫无忌,大半天意犹未尽。别前,老人家即兴铺纸,泼墨书“飞白”,瞬间,一气呵成个六尺许大大的“寿”字,令现场默默静观的我不禁倒吸口气,惊叹不已!但见,所书“寿”字,龙飞凤舞,“飞中有白,白中有飞,飞白兼顾。”运笔之妙,神采飞动,意趣横生,深得古人舒卷之法,炉火纯青,且颇具创新。
(作者系吉林省图书馆退休干部 苏 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