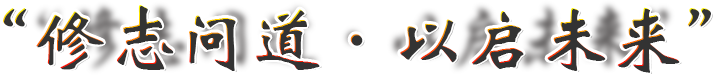高振环:贡江碑 听一个时代的潮音
1979 年9 月的一天,时任德惠县(今德惠市)水利局副局长的尹成禄,又一次走进朝阳公社(今朝阳乡)朝阳大队(今朝阳村)朱家坨子屯。来这里,是因他一直惦记着松花江边的那一块贡江碑。此处乃德惠、九台、榆树、舒兰四县交界之地。屯东一里余,是松花江滚龙一样分出的大江岔子巴彦河,俗称白浪河。“巴彦”乃满语,富饶、富庶之意。巴彦河蜿蜒流转近五十里,又与松花江合流。江岔边,有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领有的蓄养鳇鱼的鱼圈,贡江碑便立于此处。
尹成禄找了许久,却没有找到,曾经以青砖砌筑的拱形碑罩,这时惟余一片残垣。他知道,碑铭一定是遭遇了劫难,于是到小屯询问。果然,碑铭已被搬到了屯里,只是已分作三处:碑额给弄到场院,用来压生产队的打稻机;碑身垫在了生产队队部门前的路上,很多人上工前,在上面磨锄板蹭铁锨;碑座则在牲口圈里垫了马槽……
尹成禄虽然看着心疼,却又一时无力改变,遂简洁告诉社员们石碑的价值,万不可损坏了这碑。此后,他即多方奔走,终于引起县委、县政府重视,在1982 年9 月复立此碑。
贡江碑为汉白玉石质,有研究者考论,碑石应是出品于北京房山。碑铭通高3.1 米,其中碑额高0.9 米,宽0.76 米,厚0.22 米。碑额之阳与阴两面,在云纹与浪花纹间皆雕有二龙戏珠,正面阴刻楷书铭文“铭刻万代”,碑阴铭刻“铁案千秋”。碑身高1.72 米,宽0.73 米,厚0.20 米,正面楷书阴刻碑文719 字,可惜因锄板刮擦,已有137 字模糊不辨;碑阴左为满文碑文,右有汉文碑文,也都已毁坏,仅可辨识几个汉字……
艺术的残缺之美,可以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历史遗存的残缺,却只能在缺失中造成一段空白,令历史惨然失忆。还好,撰著于光绪十七年(1891)的《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记录了贡江碑的碑文。贡江碑复立时,依据此书铭刻了碑文。
从碑文可知,贡江碑应是树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以后。其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之后的一百余年里,贡江碑历经沧桑,而碑文所记也是一条江历史的沧桑。
在清初即开始的对东北的封禁,使得此后二百余年的东北山河成为封闭的禁地,山海关有关禁,柳条边有边禁。禁地之内,山为贡山、围场,江河为贡江贡河。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司采贡之职,每年依循定例向京师呈送各类贡物。松花江上,每当一过谷雨之期,网捕各种贡鱼的船只便相继轮番作业;即便严寒冬季,大江冰封,也还须按时进行冰捕,鳇鱼圈边鱼营的牲丁,须适时将圈内蓄养的鳇鱼捉拿上岸,挂冰封冻,送往北京……虽然禁令森严,一些城镇甚至施行查街制度,但大东北的空虚终究渐渐露出它的弊端,外患侵逼之下,朝廷内移民实边呼声日高,至光绪初期,实行二百余年的封禁政策实际已告废弛,大批移民涌入东北,围场出放,贡山部分出放,蒙古王公的领地也放荒招垦。正是在此背景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与郭尔罗斯王公为在此地捕鱼和垦荒之事引发争执纠纷,吉林将军衙门遂派员核同勘丈,划定各方区界,弥平争执,重归和睦。事毕,铭立此碑,详记前后因由和打牲乌拉捕鱼晾网与蒙古王公招佃开垦之界。
碑文记述: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为恪守封疆,勒诸贞珉事。窃胙土而崇国体,任倚屏藩分疆而睦邻封,谊联唇齿,此国家之成宪可鉴,边陲之经界綦严也。溯查本衙门设网捕鱼,每岁冬间,本总管奏明出边,督率官弁兵丁等,采捕鲟鳇鱼,并五色杂鲜,挂冰运署,报明将军会衔,分二次呈进。
恭祭坛庙之要贡,委非内庭口味可比。
嗣因边里人烟稠密,水浅鱼稀,前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经本省将军奏明,由边外起,南至松花江上掌,下至红石砑(砬)子、石子滩等止,其间沿江均为捕贡晾网之区。由望坡山以下,老江身分出一岔,名曰巴彦河。河西原设鱼圈一处,鱼营二所,派员看守。
唯因埋栅鱼圈需费甚巨,即令看圈官丁,在江干佐近旷地留养。条枝高大者,作栅圈障杆;细小者,为看营柴薪。按年派员上下川查,严禁私捕,侵占地址,为此办理,百有余年。敬谨奉行,委无异说。无如愚氓窥伺通场为沃土,觊觎条甸为利薮,从未歇心,迭有案据。兹遵郭尔罗斯公报请本省将军,请将巴彦河附近通场撤回,招佃输租。当经省派委员协领全福、乌拉翼领富庆、会同蒙古二品顶戴花翎梅楞吉祥等会勘,将巴彦河东岸两岔分派之间,俗名巴彦通,此通以北连脉,又名黄花岗、浅碟子、鲇鱼通等处拨给蒙古公经营,并巴彦河西岸鱼营荒甸一段,自西南第二封堆起,斜东北长七里余,由中分界,南归蒙公,北归乌署,各得一半。其巴彦河西五里通、张家湾、一捉毛、老牛圈,并鱼圈后花园通及杨家湾等处,拨给乌拉,永为捕贡之区。至于家套,仍断归登伊勒哲库站经理,与北公输租,如是拟办,均以乐从等情,绘图禀请爵帅将军希(元)批示,著照所议办理。是以于十三年(1887)四月间经本衙门署总管富庆会同蒙员吉祥,分定界址,永绝葛藤。旋蒙郭尔罗斯公来咨并函内云:除归蒙公之巴彦通业已招佃开垦输租外,其拨给乌拉附圈左右南荒场,亦令其自行招佃开垦,所收租赋津贴鱼务,以补撤出作养条场之资,永无争竞,等因遵此,足澂公爷上崇国贡,下便民生,鸿恩远沛,乌郡难名,诚恐年湮代远,罔识遵行,故勒铭永志,以清蒙乌之接界而杜永远之争端,永垂不朽云尔。
一篇碑文,一段记忆,展示的是一条江在一个时代的历史情景。原来,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在此即曾因设网打鱼之事引发过争竞,《吉林通志》记载的一件乾隆谕旨便是佐证,谕旨说:“内阁据(吉林将军)恒禄等奏,松花江下游伯都讷所属地方旗民、驿站、人夫、口外蒙古等,设网打鱼,率多争竞,请分定边界,计网征税……著派贝子瑚图灵阿驰驿前往,与恒禄、付良及该盟长等秉公查勘,分定地界,严禁越境捕鱼,以杜讼端,以资伊等生计。”当时经过勘测协商,确定了“由边外起,南至松花江上掌,下至红石砑子、石子滩等止,其间沿江均为捕贡晾网之区。由望坡山以下,老江身分出一岔,名曰巴彦河。河西原设鱼圈一处,鱼营二所,派员看守。惟因埋栅鱼圈需费甚巨,即令看圈官丁,在江干佐近旷地留养。条枝高大者,作栅圈障杆;细小者,为看营柴薪。按年派员上下川查,严禁私捕,侵占地址”,如此百有余年,不意这时又起争执。前次是朝廷派员监督勘查,解决了争端;这次则是在将军衙门督导下化解了纠纷。
还好,矛盾双方都还宽宏大度,郭尔罗斯公“上崇国贡”,深知“国贡”乃不可轻觑的要务,今次划定地界,亦是便利民生之举,尤为难得的是,郭尔罗斯公最后在来信中允诺,将附圈左右之本来不属乌拉的南荒场,“亦令其自行招佃开垦”,因此,碑文中才有“鸿恩远沛,乌郡难名”之语。只是“诚恐年湮代远,罔识遵行”,于是勒碑铭记。
参加此次分界的有“省派委员协领全福、乌拉翼领富庆、蒙古二品顶戴花翎梅楞吉祥”。但倡议立碑的似乎应是时任打牲乌拉总管的云生,因为史料所记的仓官碑,免税碑,南北贡山碑,都是立于此一时段,都是云生主其事……读过贡江碑后,如果再来看一看俗称“贡江图”的《打牲乌拉捕贡江界全图》,松花江的这一段历史情景也许就显得更为清晰了。
藏于吉林省档案馆的贡江图,已进入中国档案文化遗产名录。它与《打牲乌拉捕贡山界全图》(简称《山界图》)一样,都绘制完成于宣统年间,《山界图》由打牲乌拉翼领衙门负责绘制,“贡江图”则由打牲乌拉旗务承办处测绘完成。
“贡江图”亦附有文字说明,对乾隆二十六年和光绪十三年分界之事及后来宣统元年(1909)的事情做了注释,可补贡江碑碑文所述之不足。碑文简洁亦明瞭:地情笔记- 49 -2020 年第6 期(总第96 期)打牲乌拉旗务承办处案查捕鱼江界,于乾隆二十六年缘松江以下伯都讷属界,旗民站丁均系蒙古地方设网捕鱼,致起讼端。当经吉林将军兴(恒)禄等具奏,奉旨出派贝子胡图凌阿驰驿来吉,会同校阅大员查勘清楚,将伯都讷地方巴彦额佛罗边门外,自饮牛坑起至松江上掌牛山河止,统行划归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捕打贡鱼、晾网之区。松江以下至拉林河口止,此岸伯都彼岸蒙古,立定界限,永远封禁。倘有越界偷捕鱼尾,定必拘获,船网入官。嗣因江水频泛,网卧滚移,贡鱼每不足额,于道光三年四月内具报请,将伯都讷界内陶赖昭站站丁吴英捕鱼网卧,拨给乌拉捕打,其应征税银乌拉代为交纳等因。复由饮牛坑起至下红石砑子石子滩止,嗣于光绪十三年吉蒙乌三署派员划分江界,将巴彦河两岸五里通、张家湾、一捉毛、老牛圈、花园通暨东岸杨家湾等六处,着各通场拨归乌拉,永作捕贡晾网之地,勒诸碑石,以垂永久。乃于宣统元年八月内据总办松江邮船事宜王崇文禀请,凡松江渔户船渡酌量收捐,拟归江防经费,后经翼署以贡鱼为重,诸多窒碍等情,呈奉大帅批示,上自牛山河口起至三家子止,船渡网卧每年应纳船网课赋,拨归邮船局征收。其三家子以下至红石砬子石子滩至(止),仍归该翼署经理等因,饬知遵办在案。又于宣统元年五月内突有民人孟显成将老营通等处,指作蒙界报领,三署派员会勘划分,东归蒙古西归各署,唯如意通一段,界址甚小不堪分劈,归蒙公经理。由江心馆蒙公应得一半地内拨给乌拉六垧七亩,以补如意通之缺,立明封堆,以后江塌沙压纯任自然。绘其图说纷呈立案,是以本处遵照先令案据测绘捕贡江界全图,以期遵守,然恐日久年湮,无所考据,用注图说以垂永久云尔,理合登(证)明。
碑文与图文并览,便可清晰看到,乾隆二十六年划定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领有的松花江贡江江段,上游自牛山河起,下至红石砑子、石子滩等止。牛山河即今吉林市龙潭区江北乡的牤牛河。牤牛河实为今天的民间泛称,其本名满语“伊罕阿林毕喇”。“伊罕”,汉意为牛;“阿林”,汉意为山;“毕喇”,汉意为河。康熙第二次东巡吉林,返京时先后经过奇尔赛毕喇、布尔喀毕喇、海澜毕喇、牛磨顺毕喇……这里的“毕喇”即都为大河。牤牛河汇入松花江河口处,便是贡江的上游之起点。所说的“上掌地方”,也即指此。俗语里,指称沟川的上端与江河的上游,多说是“上掌地方”,此处是谓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驻地之上游地方。
贡江下游的端点为红石砑(砬)子和石子滩,地属伯都讷界(今扶余市域内)。从贡江图可见,石子滩上,立有捕贡江界界石。这一段松花江,长近500里左右,即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领有的贡江。选择此一漫长江段作贡江,一则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驻于距牤牛河口不过三十里的乌拉街,宜于领控下游江面;再则松花江流过丰满山口之后,乌拉街以下,江面开阔,水势平缓,乃最宜鳇鱼和各色杂鱼洄游产卵之地,且江岔纵横,多有渔获丰富的网卧,将之作为贡江,应该也是多番采选的结果。而将这样漫长的江段禁之为贡江,亦足见清廷对贡鱼的采捕是怎样的重视。
贡江虽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有,但大江两边近岸的土地却不尽为其领属。自饮牛坑附近(今德惠市松花江镇北)的“松江以下至拉林河口止”,便是“此岸伯都(讷)彼岸蒙古”。这里,此岸为北,是伯都讷副都统衙门属地;彼岸为西,是蒙古郭尔罗斯王公领地。令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频生烦恼的是,实为江岔的巴彦河,与松花江两江夹峙之间,产生一处110余平方千米的江心岛。此大岛之外,又有多处小岛,形成奇特的岛链。因为多有岛屿,江流也便弯转崎岖,岸边与岛上,树丛茂密,土地肥沃,宜放牧又宜开垦。这样的树木丛集之地,俗称“通场”,也称“柳通”。所谓“窥伺通场为沃土,觊觎条甸为利薮”,纠纷和争执也就由此而来。这便也是光绪十三年立碑和宣统年绘图的背景缘由。
“巴彦”的富饶、富庶之意,并非虚言。一百余里的巴彦通大岛,绿树参天,雉鸡飞鸣,野兔悠闲。蓄养鳇鱼的鳇鱼圈巴彦渚(亦称巴彦泡)就在这里。从此溯江而上二十里,即是舒兰法特的鳇鱼圈龙泉渚,由此向下则有如意渚、吉祥渚等多个鳇鱼圈。贡江图标示的地名里,有一处鳌花鱼圈通,显然,不仅有蓄养鳇鱼的鱼圈,也有蓄养鳌花鱼的鱼圈。
鸟有鸟道,鱼亦有鱼道。鱼会根据江水的流势,- 50 -选择自己的栖息之地与洄游路线。那里也就被称之网卧,是渔获丰盛之处。从舒兰开始,沿江两岸分布有黄茂屯、温屯、于文、江心馆、白土埃、鳌花圈通等十多处网卧。今天,仍有耆老在讲说从前“舒兰四网”“拉林十网”的捕鱼旧事,一网渔获万斤并不稀奇。时人有诗记述捕打鳇鱼、大马哈鱼之事:“射熊老手在榆关,天下精兵在此间。晓上桦船擒水虎,暮归毳帐抱朱颜……”此一“水虎”,即是鳇鱼、大马哈鱼之别称。就中已成传奇的是给鳇鱼戴笼头,鳇鱼喜欢吃江蛾,白露时节,大江上江蛾无数,几乎可以遮盖江面。它们生命短暂,存活不过几天,生命将逝时,就在大江上做最后的酣然狂舞,然后坠落江面,犹如一层白毡。喜爱静卧水底的鳇鱼,这时会浮游水面饱食江蛾,大餐之后又潜回水下。潜水功夫超强的捕鱼牲丁,看准了鳇鱼的潜卧地方,会悄悄地潜伏至前,轻轻地给鳇鱼挠痒痒,傻傻的鳇鱼自觉舒服,也即放松了警觉,牲丁瞅准了时机,就在这时冷不防地给鳇鱼戴上了笼头。鳇鱼的鼻子长,凸出于唇吻之外,这也是它又称“牛鱼”的一个原因吧?牲丁们正是利用它的这一个特点,学会了给它戴笼头。
鳇鱼给戴上笼头,鼻骨又最怕负痛,就只有乖乖地给牲丁牵着走了……这些旧时的往事,今日多已成为传说。当年那些鳇鱼圈旁,都曾设有鱼营,有兵丁驻防巡守,看护喂养鳇鱼,以便入冬后捕捞挂冰送往京城。贡江两岸,要路地方,以及人烟多处,都立有封堆,或者设立界石,严禁随意进入。今天,鱼营的营房都已不存,封堆和界石也都已颓毁不见,但多处鱼圈得到保留,圈里虽然已没有了鱼,却还在说着鱼的故事……立贡江碑时,清王朝已经近于末路;绘制贡江图时,清王朝则已是转瞬而亡。一碑一图,其意旨乃为事留凭,以期“永绝葛藤”“以垂永久”,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清王朝的大厦竟顷刻崩塌,打牲乌拉延续二百余年的采贡事务也从此废弛,当时的因事留凭,在时间的洪流里,转而有了为历史留证的意义,一个时代的潮音在其间鸣响,一个时代的故事也在那里埋藏……也许,很多历史的存留,都是这样为历史作了证明。
(作者系江城日报社专刊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