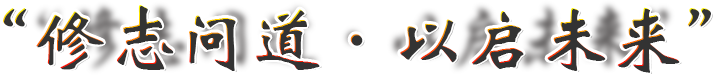“船厂”牛家旧忆
丙申岁末,作者与吉林市满族联谊会吴晓莉、市政协文史馆员皮福生两位老师来到望云山下的桃源路上,在一处极普通的民宅里,见到了从广西柳州回来侍奉母亲的牛绍飞先生。
95岁的牛老夫人刚刚睡下,牛绍飞和他二姐坐在床边,随时观察母亲的动静。他说母亲已经连续两夜未睡,这个年龄的人脑功能退化严重,经常会出现幻觉,深度睡眠几乎消失,需要 24小时陪护。兄弟姐妹年纪也不小了,他今年已经 65岁,只好轮流值守。
今昔牛家
老人居住的房子非常简陋,近乎寒酸,没有一件光鲜的物品,也许这与老人长期简朴的生活习惯有关。当然,曾经富甲天下的祖上“牛大善人”传家之物在这里更是片羽未见。但是如果留心,还是可以透过几件老物的斑驳纹理品出当年富贾大户的殷实光景。一张雕花六斗堂桌,一面纹饰木框大衣镜,一件造型精美的梳妆台,另外在另一间屋子还有几口辨不出颜色的木箱子。牛绍飞说,这都是早年父母结婚时置办的,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时尚,可惜就剩这几件,都不怎么太像样,好的早在“文革”时被毁了。那张六斗桌还是爷爷亲手雕刻的,纯手工家具。其他那些都是苏联货,当时兴洋货,从材质和造型纹饰上就能看出来,与中国传统样式完全不一样。
其实整个屋子能引人注意的还是牛绍飞父母的结婚照,他说那是 1940年拍的,可惜早年冲洗技术不行,褪色厉害,轮廓根本看不清了。另一张是1994年在日本大阪海游馆拍摄的,那时父亲已 79岁,母亲 72岁,画面上父亲敦厚慈祥,母亲一头银发,气质高雅,与眼前躺在床上的近百岁老人已判若两人。
“牛子厚的长子是牛瀚章,牛瀚章的二儿子是我爸爸牛世光,我是牛世光的四儿子。 ”牛绍飞如此简捷地介绍自己的身世。
牛绍飞兄妹八个,他排行老六,身下还有一弟一妹。六子分别“我太爷生六子七女,是:牛瀚章(喜贵)、连贵(乳名)、牛锦章、牛建章、牛平章、牛连章。牛蕴章(成贵)是二太爷(牛秉震)所生,排行老三。牛家现存的家谱我母亲功劳最大,20世纪 80年代,我和姐姐在广西工作,父母退休之后也去了广西,那时我就到了日本,在大阪桃山学院,读完国际关系学硕士就留在了当地的一家企业工作。母亲闲下来就开始整理家谱,记得写家谱的纸拖得很长很长,大约有三四米。到了 2002年,因为父亲身体不太好,我经常请假回来照看父亲,日本公司管理比较严格,请假次数多了也不好交代。2003年我就辞职回国了,专门照顾父亲。 ”
他说,那时候电脑还没普及,他从日本带回了一台,帮助母亲整理家谱,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深入地去了解并梳理牛家祖上的历史,追忆家族兴衰往事。同行的吉林市满族联谊会秘书长吴晓莉随即问道:”
“你们这支应该是牛子厚的正室乌雅氏所生吧? 牛绍飞:“对,曾祖母就是乌雅氏。 吴晓莉:”“这么说,咱们还沾点亲戚呢。 ”因为她的祖上也是乌雅氏。乌雅为满族望族大姓,正黄旗。雍正皇帝的母亲孝恭仁皇后即为乌雅氏,另外还有嘉庆帝的恩嫔、道光帝的庄顺皇贵妃也皆为乌雅人。牛子厚一生共娶一妻七妾,传六子六女(其中一子早夭),一妻即为乌雅氏,此人家住吉林北关,人称“红带子旗”,因为她的哥哥就是赫赫有名的“锡举大人”锡恩,作为满八旗正黄旗的佐领,锡恩不仅担负着驻防乌拉的旗务行政使命,同时也享受着来自皇亲的优厚待遇。
乌雅氏的另一个更显赫的身份,就是慈安太后的亲侄女儿。
吉林市桃源路锡家花园(俗称“锡家园子”)附近有个吴家坟,皮福生说,很早以前他见过一张明信片,照片上还有一块碑,查阅清末老地图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就是吴家坟,前面是炮台山。九棵树一带(儿童公园)也有锡家的祖坟,绥远将军的碑就在那里,20世纪 30年代,日本人修“神社”,就把这些碑给移到了别处。
据考证,牛家祖茔位于吉林城北沙河子(今晓光村),历史上这一带被称为“牛家山”,系三世牛化麟(1825—1881年)时期筹建完成的。茔墓占地 300垧左右,墓地有客厅、牌楼、花墙、石雕等。遗憾的是,墓碑早已在“破四旧”时被毁掉,如今不知去向,石雕更是全部被击碎,残片遍布附近山坡。
20世纪 70年代“学大寨”时,因整个山都给翻了一遍,那些精美的石刻和大石香炉砸得粉碎,所幸还能找到几块残片,透过上面精致的雕工还能看到曾经的富贵与豪华,皮福生用相机将其一一拍摄下来,留作研究资料。后来省、市电视台曾去采访,都是皮福生做的向导和解说。遗憾的是,因没有进行专门的挖掘保护,埋在土里的残片后来也不知所终。皮福生说,牛家的事情他还是知道一些,因为他和牛世光的儿子牛绍雍是中学同学,再加上平时也做这方面的研究,经常到他们家去。牛子厚因有八位妻妾,儿女年龄跨度很大,导致孙子的岁数比女儿都大。他记得 2000年牛子厚的小女儿牛淑章去世时,喜连成社社长叶春善之孙、当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中国京剧“叶派”小生创始人叶盛兰之子)还给献了花圈,如今他也已年逾古稀。
牛子厚落叶归根,子孙除有一部分移居哈尔滨、北京等地,长子牛瀚章一支至今大都定居在吉林。如今他们之间仍保持联络,延续牛家亲情。但父辈那代人健在的已经没有几位了,牛瀚章十几个儿子如今无一健在。牛绍飞说:“太爷牛子厚子孙兴旺。建国后最出息的还得算我姑姑牛立志,在延安的时候给董必武当过秘书,她的丈夫叫任建新,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如今还健在,但身体状况很不好。牛立匀姑姑只比我姐姐大一岁,小时候上学在一起玩,姑姑让大姐喊她姑姑,大姐嚷着说‘就不叫,就不叫’。”
至于牛家后人是否有从事梨园行的,牛绍飞摇摇头,稍后又补充一句:“我六叔家的一个妹妹牛先丽在吉林话剧团,但跟京剧也不沾边。太爷爷牛子厚当初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好京剧才去办科班的,祖太奶(牛子厚母亲)喜欢京剧,太爷爷又是大孝子,经常给祖太奶请戏班子来家里唱戏。有一次跟人较劲,萌发了自己办京剧科班的念头。冬天没法修戏园子,油锅炸砖,烧酒和泥,打那以后对京剧不离不舍,全身心投入,几乎到了痴迷状态,吉林市的买卖都推给我爷爷(牛瀚章)打理了。 ”
当年的牛家大院何等气派,从珲春街到和龙街,从牛家胡同到东北电院,现在唯一还能看到的建筑就是牛子厚陪嫁给小女儿的那座花园,原吉林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位置,但也已不是原来模样。
据史料记载,牛家在吉林城的住宅共有三处。20世纪 70年代,牛子厚父亲牛化麟在松江路二道码头到三道码头之间,南起松花江、北到常宁胡同(今船营区工商局附近)范围内修建了最早最大的一处宅院,总面积有 1.8万多平方米。内分五个院落,房屋二百余间,二道院墙上全部采用青砖浮雕,刻画戏剧演出场景。整个院落恢宏气派,设计精美。
牛子厚就诞生于这处老宅。另外还有两处,一是现吉林市委院内,另一处在今解放路南。
“原来是熙恰看中我老姑奶奶(牛淑章)的,要讨去做姨太太,我爷爷(牛瀚章)说啥不同意,最后嫁给熙恰的三儿子熙宏毅,那栋花园小楼就作为陪嫁给了熙家,除此之外,老宅子一间都没有了。 ”
皮福生说,1930年的时候,熙家把老宅拆掉,就地又建了一栋俄式风格的“熙公馆”,严格意义上说那已经不是老牛家原来的房子了。因为熙恰曾是伪满时期的大臣,又因为牛瀚章那个时期担任过吉林 商会会长,时这栋小楼就被当作没收,“光复”“逆产”建国后成了公产。
东北沦陷时期,牛家为了寻求政治庇护,儿女大都与权贵攀亲联姻。牛子厚长女牛淑烈嫁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之孙,二女儿牛淑蓉嫁与乌拉公馆的赵云升之子赵海功(字砚南),三女儿牛淑贞嫁与金将军家的付文多,四女儿牛淑芳(排行老五)嫁与吉林二道河子方尔康(字仲宁),小女儿牛淑章嫁与伪满洲国大臣熙洽之子。另外,牛淑章的侄女牛立品嫁与伪满洲国财政大臣孙其昌之子孙贤思……
衰落之因
1943年,对牛家来说注定是个悲喜交加的年份。牛绍飞拿出一张当年的全家福,指着每位长辈一一介绍。(牛子厚)出殡,(那一年我太爷我五叔世宁)结婚,你看照片上五叔还带着花呢,他身边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
那时候吉林的买卖已大部分倒闭,牛子厚的丧事都是在北京梨园行的友人帮助下操办的。
“我爷爷去世那年才66岁,当时全国的升字号买卖几乎都空了,吉林是牛家的发家之地,也是衰落之地。 ”牛绍飞感慨道。
由于牛子厚全身心在北京办京剧科班,生意几乎都交给长子牛瀚章打理。20世纪初的东北,正值沙俄肆意践踏之际,道胜银行操纵东北、上海等地的财政,并享有货币发行的特权,卢布(百姓称“羌帖”)成为主流货币,导致市面上一度见不到一块中国自己的钱币。
早年中俄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时,俄方曾将两亿盎司白银存入牛家恒升泰银炉金库,用以铸造银元宝给工程人员发饷银。但入库时一部分被沙俄以卢布替代,后来牛家又大量购入羌帖,结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羌帖作废,致牛家遭“羌伤”损失折合黄金达7吨之巨。
这仅仅是牛家衰落的开始。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剧,东北的出关咽喉山海关被日本人控制,东北的物资出不了关,关外特别是江南的物产也进不来,当时又面临强大的日货冲击,有人建议经营日货,但牛子厚明确表态:我也
“宁肯牛家所有商号全部关闭,不充当日本人的二道贩子。 ”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牛家在吉林的火磨厂和哈尔滨、齐齐哈尔的火磨厂向天津“永升栈”发 400火车皮面粉,行至山海关一带时遭军阀抢劫,损失现大洋一千多万。
不久牛瀚章不听父亲劝阻,私自动用牛子厚母亲遗留的黄金,到黑龙江的密山和虎林投资,以2500两黄金置地 24万垧,又用 2000两黄金从苏联购进 8台拖拉机及柴油等设备,并修建工人住宅2000余间。这些投入未等收回,九一八事变爆发,随后地产全部被日本开拓团没收。
20世纪 30年代,牛瀚章买空卖空,向日本贩卖大豆,正值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导致大豆大幅跌价,又因保管不善霉变,只好全部倾入大海,损失银圆一亿多。由此牛家正式宣布东北商号破产还债,资产被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查封,随后牛子厚到北京隐居,直至去世。
御赐“乐善好施”匾
随喜连成社的声名大振,科班学员学业不断长进,特别是一批带艺梨园世子如梅兰芳、周信芳、姚佩兰、小十三旦等入科深造,完全具备正式公演的条件。1907年,牛子厚做出决定,租下珠市口粮店对面的梨园店戏园子,准备在那里举行首次公演。
公演大获成功,得了一个“挑帘红”,一时轰动了北京城。深居颐和园的慈禧对这支梨园新秀也格外关注,以唱“万寿戏”之名通过在宫中供奉的谭鑫将科班部分演员招进宫中,专门为她唱了一年多的戏。
慈禧非常满意,要出宫时还给谭鑫培和学员们都赏了银子。过后,慈禧又特意把谭鑫培叫到宫内,说你们为我唱了这么长时间的戏,也赏了你和孩子们银两,可是你们的牛东家赏他点什么呢?赏他官,他不当,赏他银子,牛东家多得很,你说赏他什么好呢?谭鑫培也答不出来。最后,慈禧说:“叫光绪给他写块‘乐善好施’匾吧,再把仁寿殿里的陈设(包括夏商周三代鼎、刘墉字联、两棵珊瑚树、翡翠镶嵌的姜太公钓鱼的挂牌、翡翠镶嵌《西厢记》戳镜),包括我坐过的那两把椅子,也叫他搬走吧。 ”此时的慈禧离驾崩只有一年。
御赐的东西运到吉林时格外隆重,牛家人和吉林将军达桂及大小官员悉数到吉林城西欢喜岭,跪迎这些圣物。随后慈禧又下懿旨,给牛子厚建牌坊,牌坊的具体位置就在牛家坟地前,将光绪亲书的“乐善好施”匾挂在牌坊中间,两侧分别是“济贫”“扶危”。光绪这块匾既是一份褒奖,也是实至名归,因为民间早有“牛大善人”的美誉。广和楼茶园里有个特殊的阁楼,过去是皇帝赏戏的地方。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北大校长)、鲁迅(北大教员)、杨六叔(《顺天时报》)、李遂贤、辻(音shi)听花等名流经常出现在小阁楼里,牛子厚常陪他们在小账房里喝茶、看戏。闲聊中,蔡、鲁提到北京大学的宿舍、食堂不够用,影响招生,请牛子厚下个帖子,动员梨园界搞个义演,资助校舍扩建。
1919年秋,云集了梅兰芳、高百岁、贯大元、马连良、于连泉、王长林、李寿山、姚增禄、范福泰、尚小云等名角大腕的义演在京城举办了八天,票价为四块现大洋,飞票要十块一张。随后,这笔数目可观的善款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北京大学,用在了扩建食堂和宿舍方面。
据牛子厚子女回忆,当初办京剧科班所需经费都是牛子厚投资,喜连成社的一切开销,包括教师薪水、伙食和学生衣食住行及每日点心钱、房屋、水电及校内各种设备所需费用,也都是牛家投的资。从1901年到 1917年,光教师的工资就要几十万两银子,况且教师工资还要逐年递增,学生也一年比一年多。到 1917年虽然名义上不用再投资,可是科班里遇到困难还得牛家出钱,因此,牛家办这个班究竟花多少钱,实在难以估算。
但牛家从未从中分到红利,这是事实。据后人回忆,牛东家曾多次嘱咐叶春善,把自己应得的利润交到柜上,多给教师改善伙食和学生增加一些点心钱。当时牛家的生意收益确实非常可观,全国三四百家商号、作坊,喜连成科班每天的演出利润还不及一家商号的盈利,况且当初办京剧,也并非想从中牟利,因为牛东家要的不是钱,而是比钱更宝贵的京剧艺术的弘扬和传承。
“祖上创业的事情听父母偶尔讲过,但不多,只知道牛家以前非常有钱,后来就没钱了。有钱的时候日本人的校长都住我们家的房子,大清朝廷都向牛家借钱。但祖上为中国京剧事业做出的贡献,留给后人乐善好施的美名应该是最大的财富。 ”牛绍飞说。
在日本,他遇到过许多曾在中国居住过的老人,还有许多父母的同学,提起牛子厚无人不知,包括一些曾在中国居住的侨民还记得牛家的家训:要手心向下,不可手心向上。就是要多施舍,不能向人索取,这些朴素的为人之道也是牛家最大的一笔精神遗产。
2004年,“纪念喜(富)连成社成立一百周年”活动在吉林市举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叶少兰、李维康等莅临现场,并登台表演。就在这次活动中,梅葆玖盛赞喜(富)连成社是中国京剧界的“北大、清华”,这一评价得到了梨园行的广泛认同。
许多人对现代京剧《牛子厚》印象深刻,这台由吉林省京剧院精心打造、京剧名家裴咏杰、王萍主演的原创麒派剧目,自2006年开始创作,2009年9月与
观众见面,生动地再现了吉林富商牛子厚创建“喜(富)连成”京剧科班,培养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袁世海等一代京剧艺术大师的传奇经历,曾在全国各地演出数百场,轰动一时。
“大资本家”后裔
“文革”时,牛家作为吉林的“大资本家”理所当然成了专政的对象,牛绍飞他们这些后人都被划为“黑五类”,入党、入团想都别想。1968年,牛绍飞和一千多名知青插队落户到蛟河县天北公社,那是一个偏僻落后的东北山村,条件异常艰苦。后来陆续有人招工回城,可是就没有他的份,直到 1974年才调回吉林,整整73个月,这是他一天天数出来的。他说这个数字一辈子都不会忘。“出发那天是1968年 11月 23日,大家同一天出发,为什么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后来到日本留学,发现这一天被日本定为全民公休日,因为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就是这天,也是一种巧合。 ”他哈哈大笑。
下乡第一顿饭吃“忆苦思甜”饭,高粱米、窝头,大队书记上台讲话,一一介绍知青。当介绍到牛绍飞时,他站起来说:吉林市老牛家后“我是牛绍飞,
代。 ”“哎呀,书记一把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老牛家那可是大善人呐,冬舍棉夏舍单,一年四季舍粥,我爷爷都喝过老牛家的粥。有昧良心的,从老牛家打回来粥喂猪,结果遭了报应……”书记说到这里听到有人咳嗽两声,意识到说跑了调,因为现场还有“五七干校”的人,有工宣队的人,赶紧打住。
回城那天是12月23日。以往招工时一填表,人家看了就说不行,你家是资本家。直到 1974年,随着大批知青回城,他才终于把工作落实到吉林造纸厂。
吉林市造纸厂曾经是亚洲最大规模的造纸厂,六千多名职工,每日生产所需原料木材就有 1千多立方米,往厂里运木材的火车专线共有 10条。他说都是上好的原木,清一色的红松,也有少量白杨木。普通原料造出的纸印上字背面就会透过来,但吉林造纸厂的新闻纸质量品级非常高,丝毫透不过来。
牛绍飞在那里开叉车,虽然辛苦但工资不低。当时国家级“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印刷用纸就来自于吉林造纸厂,全国的出口新闻纸也只有吉林造纸厂一家。他说在
往外运纸的时候都能清楚看到,商标牌上打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根本不体现“吉林”二字。插队 6年,耽误了太多学业,开叉车的时候厂里有外语学习班,专门为工程技术人员开办的,但牛绍飞作为唯一的工人也去学习,结果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最高,总是名列第一。
特殊的家庭背景令他非常珍惜获得的工作机会,平时比别人更加努力,叉车开得又快又好,曾获得过全厂技术比赛二等奖,厂里把最好的车交给了他。那是一台日本丰田车,他拿过说明书一看,全日文的,为彻底了解这台车的性能和使用,他开始下功夫学习日语。他形容那种学习条件就像偷听敌台似的,广播教学,信号才差呢,兹兹拉拉根本听不清,晚上蒙着被子听,然后一遍遍写。
他说当时学日语也是受到科里同事的刺激,因为看到他平时跟别人不一样,总是在学日语,就打击他说,就你这出身,又插队那么多年,基础教育都不够,你学日语能咋地,“当时我就憋了还想当翻译啊。一口气,非把日语学好不可,将来就去当翻译。 ”“业大”毕业后,他想换个环境,就跑到了广西柳州五菱汽车厂应聘。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应聘者不乏“文革”前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上海交大的本科和他职大的专科PK,通用日语不相上下,但到了专业日语他们就明显处于劣势,因为牛绍飞工作时就用心钻研,汽车零件、各种工具他无一不通,最终轻松胜出。在广西作了几年翻译,后来日本泡沫经济,汽车行业陷入低谷,那是计划经济时代,与日本买卖没法做了,单位效益不好,他又做出一个大胆选择,自费去日本留学。那是 1988年,牛绍飞 36岁,这位高龄留学生以顽强的毅力远赴东洋,开始了他的求学之旅。
“单位对我很够意思,算公派自费,保留职位,工资照发,条件是学成回国工作,还与单位签了合同。 ”到了日本读语言学校半年就毕业了,但他没有如期回国,接着又继续攻读计算机专业,学制一年半。毕业后就留在日本的轻金属协会,一家代培中国留学生业务的机构,为日本企业到中国招工提供服务。
1995年,他经历了日本阪神大地震,那是一场令他难忘的重大灾难,他第一次领略到地光的震撼,经历过生死,他更加珍惜亲情,思念、 )祖国的父母亲人,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回国探亲。2003 年,为了全身心照顾生病的父亲,他放弃日本公司的高薪,毅然回国。回忆起家族往事,他说最可惜的就是大哥。“我大哥如果活着,应该是最有成就的一个,他是搞地质勘探的,东北石油学院勘探系毕业,李四光是他的大学指导老师。”
母亲年轻时在吉林已小有名气,曾在全国花样滑冰赛上荣获铜牌,牛绍飞的哥哥姐姐受其影响,体育方面也非常优秀,大姐曾是花样滑冰二级、体操三级运动员,大哥是国家级健将运动员。他们“文革”前拿的证到全国任何一个冰场都能随便用。1966年,大哥所在的东北石油学院设在安达市大庆油田,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国内资源紧张,他被派到南方找油。在一次野外勘探作业时,赶上山洪暴发,大哥不幸遇难,那一年他才23 岁。
“一米八三的个儿,英俊潇洒,兄弟几个最帅的就数他了。真是可惜啊。因为大哥长个儿的时候没挨饿,二哥就没长起来,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十来岁,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却吃不饱饭,结果就长得矮。”牛绍飞说,当时牛家孩子多,养活起来非常艰难。早年爷爷牛瀚章曾说过,要让孩子多去见识外面的世界,所以父亲从小学一直到商校毕业,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毕业后曾在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工作,并升到了科长职位。1945 年光复后,被安排在“京华火柴厂”(吉林市火柴厂前身,也是牛子厚当年资助兴建的吉林第一家火柴厂)做会计工作,直到从那里退休。
早年,牛绍飞的外公在伪满日本学校当英文老师,同时还教俄语。殷实的家境和优越的教育条件使母亲得到了良好的培养,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在这所学校上学。学校就在现吉林医学院的位置,当时叫“日本女高”,专门招收日本女学生,招收的唯一一名中国女生就是牛绍飞的母亲冯玉润,能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完全是因为外公的关系。也正因这所学校的特殊性,才使母亲得到了学习滑冰的机会。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滑冰还是新生事物,几乎没有几人能滑,女生滑冰更是凤毛麟角。吉林省的体委主任叫张文海,跟他们家非常熟悉,因为母亲经常代表吉林省参加全国比赛,每次出去都能拿回奖牌。建国后,母亲一直在吉林市中心医院做会计工作,退休后很多单位聘她讲日语,像吉林市科技馆、吉林铁路等,她又做了好几年的日语教师,直到去广西之后。
(于建青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