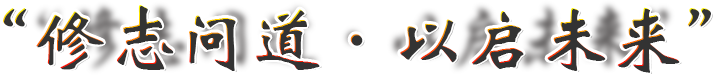《松花江上》的姊妹篇《惜别歌》 杨东阁
小序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五年,即1936年,由张寒晖作词谱曲、由瞿希贤编为合唱的《松花江上》,在关内广为流传。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十年,即1941年,由孙北、安犀创作的《惜别歌》,在沦陷的全东北广为流传。
前者表达了东北青年,在关内流亡、思念故乡的悲愤情怀;后者则是东北青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深感长夜漫漫,欲走向风沙共赴国难的深沉呐喊。
这两首歌曲堪称姊妹篇。然而后者几乎被湮没。——当时在东北青年学生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唱的这首歌,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当年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12岁(现在82岁了),那还是伪满统治时期,我小学六年级。喜欢唱,却不知这首歌的来历。这里记叙了我多年来求索的过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往事历历在目。那是1943年,伪满洲国统治时期,高小毕业的四兄东佳由家乡舒兰县赶赴省城,到吉林省立第四国民高等学校应考。折返回来时,说他此去学会了一首风靡校园的歌曲《惜别》,随即给我唱了起来。唱词是这样的:
红烛将残,杯酒已干,相对无言无言。浔阳酒醉,谁觉长夜何漫漫。共君一夕话,明日各天涯,纵然惜别终须别,谁复知见期?
关山隔,魂梦牵,无翅难翔难翔。遥望云天,怀念故人泪沾衫。劝君多勉励,愿君常欢颜,只要心心永铭记,相隔两地又何妨?!
如蛾爱火,如萤爱夜,吾辈爱难爱难。风沙何惧,昂首挺身走向前。擦干腮边泪,脱去绣花衫,温室不是我们的家,要那满天的风沙!
他一遍遍地唱,禁不住泪水盈盈。我很快就学会了。东佳说,一唱起这首歌,就觉得浑身的热血在涌动,欲奔向“那满天地风沙”。我问他:这首歌是由谁、何时创作的?他皱了一下眉头,不无遗憾地说:“不知是谁作的词,也不知是谁谱的曲。”接着郑重地说:“我一定要打听到,到时会告诉你。”
实在地说,当时对《惜别》这首歌虽然爱唱,但就我来讲,主要还是由于它曲调缠绵动人,只是朦胧感到和自己的情感相通。东佳和我几乎与伪满洲国同龄。自打记事,看到的就是日本的膏药旗和伪满洲国的红蓝白黑满地黄国旗;上学后,唱的是日本国歌“君之代”、伪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神光开宇宙”;读的语文课本叫“满语”;我和许多同学皆因未能在课堂上用日语熟背《国民训》而遭毒打;周一“朝会”,要遥拜天皇陛下和皇帝陛下;左胳膊要套上“八弘一宇”袖标;灌输“天照大神至上”,中国二字是不敢说的;在日伪统治下,民生凋敝,父亲失业,生活日益艰难;同学智文山的父亲去当劳工,走时是个壮汉,回来只见“遗骨箱”……这一切,对东佳和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记得那是1945年春夏之交,父亲得了一场大病,几近丧命,衣食难以为继。至此绝境,父亲竟出惊人之语:“满洲国不倒,我的病不能好!”父亲的话,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唱着《惜别》歌,总能感到是在抒发着一种情感,欲远别它去,脱离苦海。因此,这首歌竟使我们终生都不能忘却。
沧桑巨变。一晃我们都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的一员。1949年早春,我在沈阳请求探家获准。抵吉林时,惊悉东佳因武工队战友王树棠擦拭手枪不慎走火,击穿了他的大腿,流血过多,伤势严重,紧急从舒兰医院转到吉林市医院抢救。我马上到医院去探望,在询问过伤情之后,待要分别时,我们想起了《惜别》,便轻声哼唱了起来。这时,我问东佳:“你答应过,打听到词曲作者告诉我……”“没告诉你,就是因为到现在依然不知,”东佳说。
弹指间,到了1963年3月,父亲病故,我们都返回老家奔丧。丧事办理完毕,待要分别时,我们又想起《惜别》,合唱了一遍。东佳说,他真还留意打听过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可接触到音乐界的人,问起来都摇头,令他困惑不解。
到1975年10月,东佳从大连疗养返吉,路过沈阳。我俩到中山公园散步,东佳说:“我没有忘记《惜别》,没有忘记欠你的‘债’,只是无‘息’偿还。”其实,我也曾向多人打听过,也同样不知其作者的大名。就这样,直至1983年11月东佳去世,留下了这个不解之谜。
想不到,在东佳去世8年后,在我学唱这首歌的48年后,1991年5月17日,《沈阳晚报》副刊版,刊出署名田歌的文章:《抒发抗日情绪的〈惜别歌〉》。我赶忙拜读,大喜过望,文章说:
“九一八”事变,转瞬间,将到60周年。东北人民从1931年9月18日夜到1945年8月15日,度过了14个悲惨痛苦的奴隶岁月。尽管往事如烟,有些事仍令人难以忘怀。《惜别歌》便是其中之一。
《惜别歌》原名《风沙之歌》,为东北爱国作家孙北、安犀所作。1941年秋,孙北(当时笔名黑风)、安犀两人同到锦州,送别好友鹤琴、鹤春二人秘密去关内,奔赴抗日战场。为知己举杯饯行,孙北、安犀二人共同联句创作了《风沙之歌》。当夜共作词两段,孙北返回沈阳后,情不能已单独续作了一段。传开后,人们不知原名,都叫作《惜别歌》……
《惜别歌》先在学生、青年中传唱,很快就在全东北社会上流行。主要原因是东北人民特别是东北青年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思念祖国与反对日寇之情与日俱增。从表面上看这首歌是深厚友谊的流露,实质上是东北青年在侵略者的迫害下,深感长夜漫漫,悲愤填膺,唯有挺身战斗,走向风沙那种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的深沉呐喊。东北人民喜爱这首歌,公开传唱,潸然泪下的同时,莫不深受鼓舞。因此,这首歌完全可以和《松花江上》一歌相媲美。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笔名田歌的郁其文与孙北同为我所熟悉的《沈阳日报》资深记者。田歌的稿源何来?接着从田歌处了解到,文章所述,是孙北病逝后,从其夫人保存的《孙北诗集》里发现的。——终于破解了这道谜题。
至此,历经半个世纪,《惜别》的来龙去脉和它的作者终于了然。只是我已无法将这一切告知东佳了。在缅怀东佳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几十年间寻觅这首歌的作者,不是出于好奇之心,而是它当年使我们借以抒发了向往光明的爱国情怀。这爱国的情怀,是永远割不断的。我铭记着这首歌,怀念它的作者,却希望永远不再有人谱写这样的歌曲,再有那样悲惨痛苦的奴隶岁月。我想,东北人民的心和我是一样的。我说的这些话,也一定是东佳要说的。九泉之下的东佳兄,您说是吗?
叙一段后话。读到田歌的文章,既惊喜又懊悔不迭。我是沈阳《工人报》(《沈阳日报》前身)首批工人通讯员,经常投稿,曾与孙北、郁其文谋面受教。不仅如此,我还被报社评为模范通讯员,名字上了报纸,孙北利用我们前去领奖的机会,给我们讲过“怎样写报道”的课,我们称他为孙老师,他是乐于接受这个称呼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正在市委党校学习,心情激动万分,遂写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诗,孙北看过以后建议,不如以党校学员集体的名义写封致敬信。我接受他的意见,以工人通讯员的名义执笔写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是经由孙北删改发表在沈阳《工人报》三版头条的。毕业后不久,我被调到市级机关工作,在参加一些大型活动时,偶尔也能与孙北碰面。可哪儿能想象得到,百寻不见的《惜别》的作者竟然近在咫尺。懊悔之中,追思、冥念、深切缅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惜别》的情结促使我以后数年,时不时地想起这件事。其间,我从爱好歌曲的朋友手里得到这首歌的歌片,而且不是一种,一看歌词,同我所学的不尽相同,有的明显看出有失水准。究竟哪一个是准确的?1997年初,我想方设法查阅到一本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于1994年5月出版的《早期流行歌曲集萃》,里面载入了《惜别》歌,歌词与我所学相同,惟见标示:安犀词曲。怎未标出孙北?疑问的同时,对孙北老师的那份情感油然升腾。遂专程赶往长春,到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拜访编者吉文春。总编室主任李吉人同志热情接待了我。原来吉文春是李吉人本人、李文瑞(吉林省文联民间艺术研究会主任)和吴景春(吉林省文化厅原厅长)三人的笔名。在李吉人同志的引见下,我又拜会了吴景春同志,就《惜别》的作者进行探讨。一致的看法是,田歌的文章记述的作者,创作的时间、背景,所依据的是《孙北诗集》,应视为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据此可以推断,《惜别》当属孙北、安犀共同创作。吴景春、李吉人二同志表示,《早期流行歌曲集萃》再版时,将标明:《惜别》——孙北、安犀词曲。对此,我深表赞赏。这样做,对音乐界来说,是一件幸事;同时,堪可告慰于已经作古的孙北同志。
时光又流逝了14年——2011年, “九一八”事变80周年,我想就此写一篇纪念文章。动笔后发现,作者其人在田歌的文章里只有一句话,“东北爱国作家”。我查遍了东北作家群的相关资料,无所收获。可我决心就是挖地三尺也要弄个水落石出。冥思苦想,电话无数。终于想到一位——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崔玉化同志。电话里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回答得干脆:“老领导交办的定会尽心竭力。”时间仅隔一天,他便把我所要求的办到了。
崔玉化向我提供了《沈阳日报60年》纪念集,该集在“创刊时期”章节里,明确记载:1948年沈阳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安犀(即安西)与孙序夫(孙北)受党的委派已经在报社(国民党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创办的军报——《前进报》)工作了。他们以记者身份从事情报工作,还分别担任了编辑主任和采访主任。
又记载:孙北,祖籍山东,伪满时期(沈阳)同文商业专科学校毕业。1945年在重庆参加革命,日本投降后被派回东北,成为第四野战军所属地工组织成员。后来,被党组织派《前进报》做记者工作,《前进报》被接收后,留报社工作。曾任政教组组长、夜班总编室主任、编委。“文革”前调离报社。1980年因肺癌去世。
这是巨大进展,但语焉不详。在接续下来的时间里,我将注意力瞄准在寻找《惜别歌》作者的亲人方面。终于寻找到孙北的夫人——《沈阳日报》资深记者、离休干部宋阿芳和安犀之女——沈阳大学退休教师安保良。她们提供了详细而准确的情况,不仅如此,还提供了孙北、安犀的照片。所得一切超出了我的期望。幸甚!
孙北原名孙序夫,受组织派遣回东北干“地工”遂改名孙北。孙北1922年出生于沈阳高级技师家庭,沈阳同文商业专科学校毕业,从事新闻职业,1943年流亡到重庆,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6月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地下党,与同为地下党的安犀(改名安西)一起,被派为我军“四野”的情报人员,安犀任国民党军军报《前进报》编辑主任,孙北任采访主任,他采访过“东北保安副司令”马占山;1948年北平发生“七·五”惨案,亲去北平采访,连发报道,揭露反动当局。此时,孙北已是知名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孙北不到场是不能开的。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我党接收了《前进报》,陶铸创办了沈阳《工人报》(后为《沈阳日报》),孙北为业务骨干,担任编委、政教组组长、总编室主任。1954年与小他10岁的同事宋阿芳结婚(婚后无子女)。1955年在肃反、肃胡(风)中受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右派集团骨干,被清除出党,送劳动教养(发生活费18元);几年后摘掉右派帽子,由行政14级降到20级,分配到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铁西分理处干业务。“文革”中惨遭批斗。1970年1月携妻到辽宁兴城碱厂公社插队落户;1978年回城;1979年由沈阳日报社党组织为其右派予以改正,恢复党籍和原级别。此时孙北已肺癌晚期,于1980年辞世,终年58岁。
安犀1914年出生在沈阳,父亲是人力车夫,小学学历,自学成才,青年作家,早年著有小说《山城》、剧本《姜家老店》,经常在《电影画报》上发表评论。新中国成立前为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被抽调,参加沈阳市郊区“土改”工作队,搞“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后来留在马三家子区,负责区政府的领导工作;再后来,发挥其业务专长,调到沈阳评剧团写剧本;不久,上调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戏剧改进科搞业务指导,还曾受到文化部刘芝明部长的鼓励呢!1954年8月大区撤销,调中国戏曲研究院,旋调中国评剧院专事创作,写出《向阳商店》等优秀剧目。在肃反、审干运动中受审查,长期背着有历史问题的政治包袱,“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请病假回到家中,突发脑出血离世,终年58岁。
《惜别》歌曲创作迄今已经七十多年了。两位作者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尤其是孙北,令人痛惜。铭记《松花江上》,勿忘《惜别歌》。诚谢多年来为搞清有关它的一切帮助过我的人们。——我自己则获得了一份快慰!
(作者为沈阳市委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