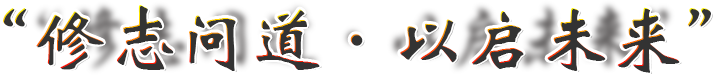略议人物传的记言
我国古代史志的人物传是有记载传主言论的传统的。如《史记》写项羽见秦始皇出巡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写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写陈胜反秦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三个人三种口气,均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他们不同的出身、性格特征与抱负。《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初见刘邦论刘邦、项羽形势优劣及刘邦应采取的方略,《三国志·诸葛亮传》记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的隆中对策,都是记载传主言论的精彩之作。《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中还提出“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的主张。“论”,择也;“可论者”,即值得选择者。以此,《史记》相关列传中录有《说难》《黄歇说秦昭王》《乐毅报燕王书》《鲁仲连遗燕将书》《怀沙赋》《谏逐客书》《过秦论》及主父偃上书和贾谊、司马相如等的文赋。史学大家翦伯赞评论《史记》记言说:“他撰伯夷,则录其《西山之歌》,以显其气节;撰孔、孟,则录其言语,以显其大道;撰老、庄,则录其著作,以显其学派;撰屈、贾,则录其辞赋,以显其文章……”2
章学诚也主张在志书人物传中载言。他说:“学士论著,有可见其生平抱负,则全录于本传;如班史录《天人三策》于《董仲舒传》,录《治安》诸疏于《贾谊列传》之例,可也。至墓志传赞之属,核实无虚,已有定论,则即取为传文;如班史仍《史记·自序》而为《司马迁传》,仍杨雄《自序》而为《杨雄列传》之例,可也。”3他所纂《和州志·成性列传》就记有多次上疏的内容。
要重视记言还因为,除言行不一者外,一般有懿行者多有嘉言。如孔子所云:“有德者必有言。”4古人倡导“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统帅,事功与言论则是道德高尚之人的两个重要方面,不可偏废。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名人的言论多么精彩、鲜明、生动,切近其职业特点和性格特征,或表达了独有的看法与思想感情。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座右铭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其雄心壮志可感可佩。大画家齐白石有名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是他一生绘画艺术的深刻总结。教育家、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对大学实质的精辟判断。建筑学家贝聿铭认为,“建筑和艺术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一致的,我的目标是寻求二者的和谐统一”,表达了贝氏视建筑为艺术的见解及对建筑艺术的孜孜追求。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经常向前来参观的客人指着豌豆十分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我的女儿。”对自己研究工作的酷爱溢于言表。例证何止万千,就此打住。诸多精言妙语怎能不用在传记里?
如何记述传主的言论?一是要广征博采。不仅要搜集传主说过的话,书面材料,举凡著作、文章、书信、诗词、笔记、日记、电文、调研报告等都要遍览,从中摘取表明传主心迹或与事迹密切配合的精辟言论。如《尚志市志·赵一曼传》用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的《滨江抒怀》诗,抒发她抗日的坚强意志:“未惜头颅新旧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最后录给儿子宁儿的遗书。《绍兴市志·鲁迅传》则记载了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鲁迅与茅盾向中共中央拍发的电报:“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二是要取精撷要。一定要选入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精要言论。《绍兴市志·秋瑾传》记述“鉴湖女侠”秋瑾在就义前面对审讯奋笔而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表明她对时局的愤懑和无奈。当时正是农历六月初六,天气溽热,秋瑾感受的却是满目肃杀的秋雨秋风。实际上,在秋瑾就义前几天还有一些言论,如古轩口就义前五天给好友徐自华妹妹徐小淑写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
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表达了秋瑾面对同胞梦醉、祖国陆沉,而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以及不弃责任、不畏牺牲的情怀。
即将就义时,有兵士欲拽秋瑾前行,秋瑾怒目而斥:“吾固能行,何掖为?”到轩亭口,秋瑾立定,对刽子手淡然一笑:“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乃张目四顾,复闭目曰:“可矣。”遂就义。表现大义凛然。
然而,这不是秋瑾的专传——专传必录之,而是《绍兴市志》人物传之一,字数有限,所以,只用“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表达秋瑾的心情,足矣。
其他像《苏州市志·范仲淹传》引用其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绍兴市志·嵇康传》引嵇康在临刑时说的话“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表其持才自负。均极精短。
三是要言论有出处。不论是话语还是文字,都必须有文献记载的依凭,编者不能想象发挥。有论者认为,可以根据事件的大量史料和现场氛围,设想人物话语。举例则有《左传》中记载的介之推与母亲的一段对话和《史记》中鉏麑自杀前的慨叹。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赏赐跟随他逃亡的人,介之推没有提及禄位,也没有得到禄位,感到难与相处,欲亡。“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尔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宣公二年,昏庸残暴的晋灵公对向其进谏的赵盾怀恨,派大力士鉏麑去刺杀赵盾。第二天早晨,鉏麑走进赵盾家院内,见赵盾已穿好朝服准备上朝,因时间还早正偷空打盹。鉏麑见此情景叹气自语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名,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说完触槐而死。如此私密谈话和自语,没有文献依据,自然引起后人的怀疑。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一卷中说“上古既无录音之具,不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勿密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回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他对两处话语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在文史不分家的《左传》《史记》时代,这样做可以,也很形象生动,但当代修志重实录,编者是不可以代拟其言的。(梁滨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