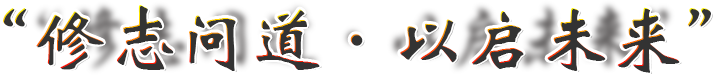《人物传记》之我见
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批示中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 ”简短的几句话把修志的性质、作用和要求提得十分明确。我觉得志书的质量,是编修工作的第一位任务,也是衡量编修工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现以一部县志的《人物传记》为例,看某些志书在编纂质量上的问题。这是《××县志》(1985~2000)《人物篇》中“人物传”内容:(一)列入“人物传”者 24人,全县总人口 34.5万,仅占万分之零点七。(二)在 24名“传主”中,副处级以上地方官员 10人,占 42%……(三)没有一名女性列入传记。例如:在一名“传主”的名下,这样写道: “×××,1928年生于 ××省××县, 1937年就读于 ××县 ××小学, 1947年毕业于 ××县中学。 1949年至 1950年,任××县人民委员会科员, 1950年至 1951年任××县××区政府副区长。 1951年 5月至 12月,任黑龙江省赴朝鲜医疗队队长。 1952年 1月至 10月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秘书。 1952年至 1956年,任中共 ××县党训班干事、副主任。 1956年至 1957年任中共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1957年至 1958年任中共 ××县××乡总支委员会书记。 1958年至 1961年,作中共 ××县××公社书记。 1961年至 1963年任中共 ××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 1963年至 1965年任中共 ××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 1965年至 1966年先后任 ××专署水利工程处政治部主任、中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1978年任中共 ××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980年 9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6年退休, 1987年病逝于××县。 ”
这则人物传记“简练”得到了只有“简历”的程度。根本看不出褒贬,更不要说业绩了。在该书入志的 10名地方官员的传记中,竟有 6名都与此雷同,这里不一一列举。
如果说第一轮修志仓促上阵业务不熟,没有经验,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可以理解;全国已经进入第二轮修志,在公开出版的志书中竟存在如此问题,即不可思议又不可原谅。犹如人的身体,不管那个器官出现病变,都会影响到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志书也是如此,它是一个整体,无论哪个篇、章、节、目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整部志书的质量,会给志书带来致命的伤害。对这个问题,我疑惑不解,想探索一下原因,于是设法联系上了该书的一位副主编。他不否认这些问题,但强调了一些客观原因,似乎也有些道理:“入志人物数量偏少,是因为没有掌握那么多,
又来不及调查走访,让下面报,又报不上来;入志‘人物传’中副处级以上者偏多,是因为县里统一划了个‘杠杠’,凡副县级以上者可以入志,至于事迹是否突出,没人过问;是否应该有女性人物入志,没有考虑那么多,有所忽略。 ”
我很理解这位副主编的苦衷:他只是一个执笔者,虽然委以重任,但名列他之前的有主编、责任主编、执行主编,他这样一个被聘任的退休人员,怎么能违背领导旨意呢?况且之前也没有修志经历,这次参与修志也是现学现卖,照葫芦画瓢,能够出一本书,完成任务就很不错了,那里还顾得上什么质量不质量的问题。
从这部县志《人物篇》“人物传记”中暴露出的问题看,某些编纂者对入志人物的认识、衡理标准以及具体写法都存在不妥之处,这不仅仅是数量问题,而涉及工作态度和唯物史观。
先说入志“人物传记”数量偏少的问题。从辩证关系上,没有一定的数量,不足以反映质量,一个具有三十几万人口的县份,列入传记人员仅万分之零点几,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本应成为历史的主人。尤其是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人为本”的时代,反映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修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从实际情况看,远的不说,仅近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人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创造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于改革开放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开拓进取、勇于探索,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先进模范人物更是数不胜数。怎么会感到没有几个人物可写呢?关键是我们的思想没有解放,还没有放开脚步走出去,只是局限在书斋里,等着下面上报,而基层干部和群众又不掌握入志人物标准,怎么能将你所需要的如实上报呢?“站着看不见蚂蚁,蹲下去看到满地是蚂蚁。 ”选择出那些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乡村干部、能工巧匠、种田能手、畜禽专业户、道德模范、乡村教师、医生和舍己为公、助人为乐者,以二十年为时限,在有三五万人口的乡镇里,选出十个八个来都不算多,三五个总可以做到吧,全县共有三十个乡镇,以此推算,百八十人入志不是难事,即使如此这也仅仅占到千分之零点五。我反复强调的比例,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
其次,对地方官员入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协会多次会议纪要上,都强调入志人物不要以职级为标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高官贵族未必具有高尚的人格价值,平民百姓中亦有许多道德高尚、品质优良者,人格价值与人们的地位贵贱不一定成正比。这里面涉及一个认识问题,不同社会对人的价值衡量标准会有不同: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起决定因素的是出身门第;在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于金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包括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也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至于地方官员能不能入志,关键要看他的人格、品德、觉悟和业绩,即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如果我们的志书编纂者受惑于金钱和权力的魅力,沉迷于现实的浮华与喧嚣,在经济社会变型时期,面对传统理论、是非标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能很好掌握标准,把握尺度,就会失去基本的坐标和底线,把那些虽然具备入志职级,但政绩平平,群众口碑极差者也混迹于志书当中,那么志书的存史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现实作用也值得怀疑。当然地方官员中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不能绝大多数都能入志。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一定要为他们树碑立传;即使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但作风朴实,廉洁奉公,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戴和好评,也应该入志立传。
一些地方之所以存在以“职级”作为入志标准的问题,引用董一博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以一定职级作为立传或入志的标准,似乎减少许多麻烦,实际上是庸人之见,还没有摆脱等级的观念,旧的传统影响。 ”也不排除某些地方官员中存在着的“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在作怪。
三是关于为妇女人物立传,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妇女都是一支重要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的今天,妇女更是撑起了半边天。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各行各业涌现出的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道德模范、持家能手,都应该为她们立传。从社会学、妇女学角度看也不应该将他们遗漏,从社会主义制度上看男女平等,在志书的人物传记中看不到这些,既不公平也不公正,更不符合实际情况和时代精神。
据《中国地方志协会 1989年学术年会纪要》“妇女立传人数只占 1%至3%,甚至有的志书没有为女性人物立传”。这里我提点建议:不妨设点硬性规定:妇女立传人数占 5%至10%如何?我觉得这不是妇女中有没有这些人和是否具备入志标准的问题,而是缺乏具体调查和深入发掘的问题,因而不被我们所掌握,如果改变思想转变作风,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从《××县志》反映出的问题看,在修志队伍中确实存在着水平不高,能力低下,敷衍应付的情况。从 20世纪 80年算起,至今修志工作已经三十几个年头,这些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早应该解决,但从一些县级修志情况看却不尽然。而其症结,以我个人之见,主要在志办主任和主编身上。有的把志办当作跳板,通过这个“冷门”提拔上来,干个两三年再跳出去;再调来一个,仍是如此。这种“走马灯”式的频繁换防,人都安定不下来,又怎么能潜心修志呢,志书质量也就无从谈起。修志工作是一项连绵不断的事业,需要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当第一轮修志工作结束,随着老一代方志人的退去,修志人员的宝贵经验,奋斗精神,优良传统,也尽被带走。
新的一批人员上来,仍是仓促上阵,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这种状况与修志形势的要求大相径庭。长效机制变成了短期行为;良性发展变成了恶性循环;专业技术人员变成了门外汉。当每轮修志结束之后,即“旗倒兵散”;下一轮修志开始时,又重新“招兵买 马”。这种状况不改变,修志工作难以为继,质量问题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与部分代表的座谈中强调,要把地方志作为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切实抓好。要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佳志。
提高志书的质量标准,打造精品佳志,这是对修志最基本的要求,应该贯穿到编纂工作的全部过程,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无论志书的那一部分,那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志书的整体,因此必须提高全方位的质量意识。我的看法是首先要从源头抓起。早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把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是要选好志书的主编和总纂; ”更要把住收口,中国地方地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在制定规划时,就可以考虑把加强志稿审读,严格志稿验收,提高质量标准,“有的省志办又作为突破的重点”进一步酝酿出台‘驳回重修’制度,建立专兼职结合的专家评审队伍”。我觉得,采取这样从“源头”到“收口”的双保险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志书质量。一旦发生质量问题,“驳回重修”也是必要的,这体现了严肃认真的负责精神。
写到这里,笔者又有一点想法,围绕质量问题,可否在措施上多做些文章,加大些力度,比如,借鉴某些行业的做法,每轮修志结束后,全国或每个省评出一、两部“最差志书”,或采取“末位淘汰制”进而使编纂者感到压力,产生动力,感到这“志”不修不行,修不好也不行;同时也倒逼地方政府遴选好的主编或总纂去具体做好编纂工作,克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积极认真地把好志书的审查关,从而有效提高志书质量。作为修志工作者,重任在肩,担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神圣历史使命,要通过我们的努力,修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为读者和后人奉献出真实可靠、质量上乘的合格信史。我们一定要做到像李克强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批示中要求的那样,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赵福山 作者系吉林省通榆县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编审)